我的任务首先是恢复历史真相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
历史本身没有国界和政治性,但是历史学家有国界限制,我们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然而,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是研究真实的历史,这才维护得了。
葛剑雄教授今年80岁了,这位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经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如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精力充沛。6月13日这天,从下午到晚上,他有两场媒体专访和一场在书店举行的活动,始终未现倦色。
我问他在身体和精力方面感觉如何,他说没有问题,还在做着正常的工作,一天两三场甚至感到“轻松得很”。他说,自己的观点是不要主动迎合衰老,认为到了某个年纪就不能做某些事情,是不正确的,反而会衰老得快。
历史学者张宏杰是葛剑雄的学生,他在文章《我的老师葛剑雄》里,叙述葛老师的三个突出特点,第一个就是超乎常人的精力充沛和勤奋。他是不用手机的,只用邮箱联系,密集活动的午餐间隙不休息,在飞机或高铁上,更是不休息,而是在工作,在谈话,在写作。
因此,他留下了如此多的文字。今年新出版的两本文集收录了他过去十年间的文章,通览下来,不得不感叹他的经历之丰富,涉猎之广泛。与人们通常对学者终日苦坐书斋的想象完全不同,他喜欢东奔西走,自述三个月走进非洲,三个月往南极科考,两个月重走玄奘路,所去之地,远至北极点,高登乞力马扎罗山,而与此同时,他写作、主持编写的文字,怕有上千万字之多。
他曾在2008—2018年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成员,与国家相关决策部门和国家领导人多有接触,所以看他的文字,同他交谈,能够感受到他的位置角色所赋予他的言说方式,与其他并不具有如此身份的历史学者的区别。或许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常被人称为敢讲话的“葛大炮”,另一方面,又容易引起同一拨人的非议。几年前,他正因为一番在他看来颇为正常的讲话而引起民间学者的批评。
以我的观察来看,葛剑雄教授并没有变,在这次采访中,曾经引起讨论的话,他仍然如常地反复言说。在别人看来会矛盾的地方,他处理得成熟而坦然。或许,他们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批评者想象的那么大。现实的决策和选择并非历史学家所做,作为历史学家,葛教授完全同意并坚持表达的是,首先要尊重历史、研究真相、普及常识,在这一前提下,决策者才有可能做出积极的、明智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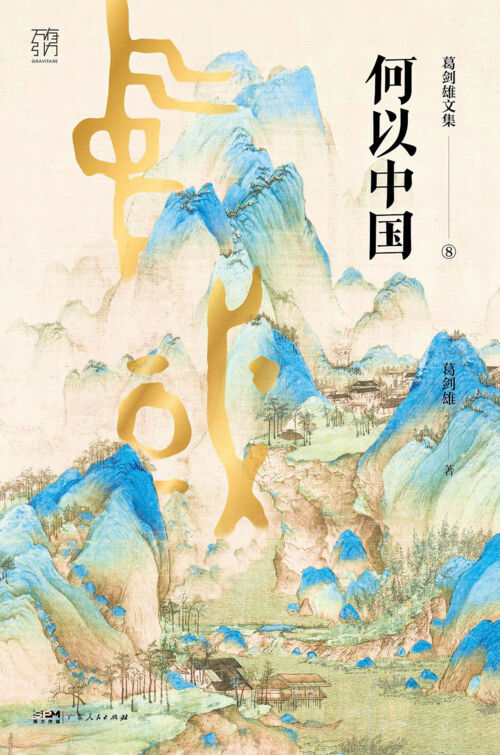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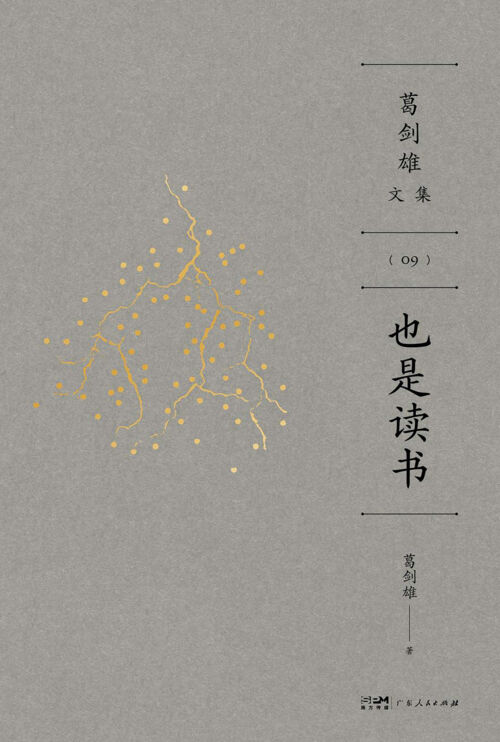
《何以中国》《也是读书》
研究真实的历史
南风窗:今年出版的两本文集收录了你过去10年的文章,现在回顾,你是什么感受?
葛剑雄:2014、2015年,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集,有7卷,内容是我70岁以前的,这次出了两卷续集,收录了我70岁到80岁之间的文章。
我写的序言、前言、后记、书评较多,所以编写了第九卷《也是读书》。我认为,为他人撰写序言,前提是也要认真阅读,这些也是读书的产物,所以用了这个名称。
第八卷是《何以中国》,这一卷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地理、丝绸之路、长江黄河、运河等等,并非专著。这里面也收了一篇我以前编的秦汉史教材,它是作为大学里面的选修教材使用,公众通常看不到这些内容,所以我把它放进去。还有一篇是我给科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写的总序《何以中国》,里面的内容可以涵盖这本书,我就把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
大部分文章是前几年写的,有一篇《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历史地理学的使命》是交稿以后再补进去的,我认为这篇比较重要。
南风窗:近年中国人对何为中国以及身份认同的问题越来越在意,有些人看到某些形象和表达,会认为这不应该是代表中国的形象,是对自己的侮辱。你一生都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这些年你对什么是中国有新的思考吗?
葛剑雄:如何理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这里面有不同方面。重要的是史实,需要通过考古、分析文献才能知道。作为历史学者,我的任务首先是恢复历史真相。可惜现在对许多常识,大家的认识都并不准确。所以我这些年做的事,是尽量纠正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对所谓常识的理解。
例如,我发现大家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误解很深,充满夸张,甚至根本不了解这段历史。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才提出来的,而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很片面。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也不是原来有的,是到1968年日本人(三杉隆敏)提出来的。中国古代很少有过主动的外贸,有的多是走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时,认为自己的资源足够,不需要外面的东西,是别人需要我们。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外国人主动开辟的,他们对中国有贸易需求,但现在不一样,是中国主动。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并非是对丝绸之路的重复和重建,它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思考的是,它的创新之处是什么?今天我们如何能吸引外国人,如何取得他们的配合?怎么样才能建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其实这并不容易,沿线的相关国家历史民情都很复杂。比如,我们在巴基斯坦建立的中巴经济走廊通过俾路支省,这个省的面积占巴基斯坦总面积的44%,这里也是最贫困、最复杂、最乱的地方,暴力活动频繁,政府管不了,很多地方要部落长老来管,这些历史背景我们都应该及时了解。
这些话我持续地讲,一开始大家还不容易接受,十几年过去了,一些人告诉我,现在都慢慢接受了我所说的。
我认为历史本身没有国界和政治性,但是历史学家有国界限制,我们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然而,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是研究真实的历史,这才维护得了。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探讨边界的历史。例如,有些争议地区是否属于古代中国?尽管研究结果并不都对中国有利,但如果不进行研究,我们如何做出明智的判断和选择呢?如果要认真研究历史,就不能回避历史上的矛盾和困难。
致力于普及工作
南风窗:最近一个历史小说改编的影视剧《长安的荔枝》在播出,它讲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小小一颗荔枝,从岭南长途跋涉运到长安皇城,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有一则视频将成本折算为如今的价格,据说要40亿。按理说这是很大的浪费,不过在视频下,不少留言认为,运送荔枝也创造了很多就业。
葛剑雄:这种回应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运河,连一些专家都不知道,大运河的成本非常高。在山东的丘陵地带,运河河床比两边的土地高出近40米,要通过建一座座船闸来拦蓄,再逐级下泄降低水位,修建和维护成本非常高。山东丘陵又干旱缺水,为了维持运河水位水量,连山泉水都要控制起来,每个泉水口要派一个人看管。官府规定,只要船没有过尽,哪怕农田干旱,也得保证涓滴不许外流。
有人说,运河在历史上沟通南北经济和人员往来,这不对。漕运任务未完成前,是不允许民船使用运河的,民间货物往往通过走私买通粮船夹带,属于腐败行为。其实官员也不能随便使用。曾有规定,有5种情况才可以动用运河,比如5品以上官员死后棺材可以通过运河,亲王可以用,外国使者可以用。我查阅过明朝和清朝那些人留下的日记,绝大多数人是没有从头到尾坐运河的,平民不让用的。
多年来我们始终强调并且夸大了大运河的优点,这导致很多人对运河的常识都是错的。有人说,运河恢复后,要乘船从杭州到北京去,我告诉他们运河的这些情况,他们很惊讶,“啊,还有这样的事?”
又有人说,我们要大力发展运河旅游,他们也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水本身没有观赏性,都是要借景的,当你在巴黎塞纳河上乘船,看的都是左右两边的景和建筑,不是河里的水。我们站在船上,几分钟后就会视觉疲劳。有些地方要保证基本运河航行,就不能再去搞旅游添乱。
还有人宣传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从水利角度来看,沟通五大水系有利有弊,沟通了水系,也把自然灾害带到那里去了。黄河历史上夺淮,就是通过运河的水道,侵入淮河,把淮河下游作为黄河,最后把下游全部淤没。明清时,黄河发大水或者决口,官府甚至规定不许堵口,不许治理,要先保证运河里的水多,宁可保运就不治黄,山东和河北为此都要做出牺牲。
南风窗:你认为历史方面,我们今天还需要普及哪些常识?
葛剑雄:还有长城。长城本身是一个防卫工程,现在有人说长城并非封闭,而是开放的据点。长城何时成为开放的据点?是长城的功能被废除后。清朝康熙皇帝时,人们说修长城,康熙说“修什么长城?蒙古人就是我的长城”。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长城上的关口就成为了交通要道。
曾有说法很流行,说长城是唯一在太空中用肉眼可以看到的。我当时认为这不可能,写了文章,这篇评论在那年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三等奖、上海新闻奖二等奖。我的理由是,长城难道是地球上目标最大的地方吗?比它大的建筑还很多。第二,宇航员得知道这里叫长城。第三,正好他没有睡觉,而且下面还没有云。后来,物理学家通过测算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需要纠正大家对历史的误解,并补充一些该有的常识,我甚至认为这个意义已经超过了我们做自己的研究,当然科学研究非常重要。
这些年我自己重要的内容通常会分为三种,一是学术专著,二是中等程度的学术普及书籍,还有一二十万字的公众普及读物,我认为这样才能在学术与社会之间起到沟通的作用。
比如,我主编的《中国移民史》六卷本,此外,我们编写了一本四五十万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并且还出版了许多关于移民的小册子。最近要出版一本《中国移民3000年》,首先在爱奇艺上制作视频,然后会记录并整理视频文字,这样普及面就广了。
我主编了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共400万字;我还编写了一本30万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此外,还有几本几万字的书和许多文章。
这些年我花费很多精力进行普及性讲座,并且制作了一些普及性小册子和文章。我希望这些东西都能起到启蒙的作用。
南风窗:正如你所说,常识的错误俯拾皆是,你做普及性的启蒙工作,会不会有感到挫败的时候?
葛剑雄:如果我们不承担一定的责任,实际造成的是国家的损失。

北京司马台长城(图/视觉中国)
正在考虑人类文明的两条主线
南风窗:这些年,公共领域的历史热集中于微观史著作,比如北大罗新教授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澳门大学王笛教授的《茶馆》《袍哥》,小人物的故事受到读者的欢迎,不像十多年前,还是大历史流行。你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个现象?它在历史学科内部产生了什么影响?
葛剑雄:其实这两方面不能偏废。宏观由很多微观构成,没有微观不可能架构起所谓的大历史。第二,大历史需要价值观念支撑,不是范围大才是大历史。宏观不仅是事实,更是如何解释和构建,这才是大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少限制,往往写不好大历史。
我曾在小册子中写到,历史的最高境界是历史哲学、历史价值观,而非具体研究。人类的科学和人文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和信仰,如果我们传统的历史观无法突破,谈何大历史观?
另外,这与我们长期的学风学派有关。比如日本人的历史研究,一直是微观的道路,日本也有历史大家,对中国的历史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但是到后来也越来越趋向于做小题目。他们的优势是能穷尽材料。
例如当年研究郑成功,中国人限于中文材料。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娶了日本的太太,郑成功在日本生活到6岁才到福建,日本研究者收集了相关的日文材料,另外郑成功与荷兰人打交道,他们又跑到荷兰,果然也找到很多资料。日本人做的题目有时候超过中国人,因为他们对资料的收集点滴不漏,而且有耐心,有可能研究一个人就要研究一辈子,但缺点是没有整体性。美国人动辄一个框架,一个模式,胆子大得很,3条史料就可以产生一个理论。
中国应当吸取美国人的整体研究观,同时将日本人的精细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具体到个人,我认为不能要求他两者兼顾,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有所选择。
这些年之所以微观史受欢迎,也因为我们历来缺少好的微观研究,王笛和罗新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另外这几位都接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是高手,由他们来才可以,如果换其他人,未必做得出来。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们并不具备做大历史的条件,与其做得大而无当,还不如不做。目前有资格做大历史的学者不多,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是语言障碍,只懂英文还远远不够。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懂一门外文已经很不错了,研究欧洲历史,如果不懂拉丁文可以吗?研究世界历史,得了解宗教,了解基督教。
汤因比写了二十几个文明,但他讲中华文明明显有些地方是错的。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有些做大历史的人都是一个团队或者有很多助手。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实际上好多都是中国人帮他写的,生物部分是鲁桂珍帮他写的。
像《人类简史》等作品的普及程度和可读性很高,这些作者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学术界认为他们不严谨。只有不严谨的内容才能吸引人。许多作者都是新闻记者出身,他们收集资料可以,但是在解释资料时,往往根据他们的历史观来解释。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受欢迎是特殊情况,当时中国正处于刚开放不久的时期,他采用美国的叙述方法,这种表述让中国人耳目一新,加上翻译非常出色,是廖沫沙帮他润色修饰的。黄仁宇的博士论文通过都非常勉强,他的教授职位最后也被终止,美国历史学界并没有充分肯定他的贡献。
南风窗:你说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历史价值观和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
葛剑雄:我在考虑人类文明的两条主线,一条是科技物质的主线,一条是精神人性的主线,如果考虑周到了可以作为大历史的题材。我认为,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发展,精神提升和思想飞跃也相当重要。这个过程不能通过群体,而是通过个别杰出人物实现,而且那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往往违背当时的地理环境。
南风窗:有没有考虑思考成熟的时候出专著?
葛剑雄:那没有,不可能的,很多问题要等到脑科学突破,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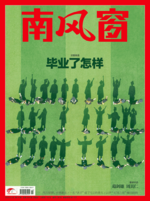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