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救护车,围猎转运病人
如果病人最终上了一辆黑救护车,只是因为他们没得选,而他们仍想赌一个生机。

AI创意图(制作/郭嘉亮)
女儿死后,张凤琴才知道,她们上的那辆停在医院里的救护车,根本不是医院的救护车,随车医护也不是这家医院的人。
叫车前,医生提醒张凤琴一家,当心外面的黑救护车,要找车身有他们医院标识的。对这对靠种地和低保维生的夫妇来说,“有医院标识”成了他们分辨救护车合规身份的唯一线索。
2020年8月5日上午,家人照这个标准找了一辆,给跟车医生转了1万元,推着患有罕见免疫性疾病的女儿上了车,紧急从长春转至北京求医。从长春到北京,车程约12个小时,上路不到1小时,意外就发生了。
供给女儿的氧气不够了。为此,救护车两次下高速,去找氧气瓶。家人提出要看监护仪了解生命体征,医生阻拦。之后,女儿心率下降,被注射了抗心衰的药剂、进行胸外按压,家人却看不出有更多急救设备。
张凤琴称,最终女儿于当晚死亡,而车行至北京通州,尚未抵达目的地,就连夜返回了长春。
张凤琴一家为此打了4年官司,2024年6月,终审判决书认定:“(涉事车辆所属的)急救站在其配备的医护人员、急救设备、执业资质方面均不具备对危重患者实施急救的情况下,承接了病危患者的转运业务,又因配备氧气不够充足,中途两次加氧气延误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客观上加大了患者丧失救治的几率,应对患者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院判定,急救站承担60%的赔偿责任,而医院放任急救站在院内招揽业务,未尽监管责任,承担10%的赔偿责任。
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黑救护车”的围猎下失去了救治的机会,也点燃了普通人对黑救护车的担忧。它们围拢在医院周遭或停放在院内,混迹于常规救护车之间,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成为各方“默许”的一门灰色生意。越是医疗资源紧缺的地方,乱象越是突出。
黑救护车围住医院
多年前,国家应急医疗专家、原平顶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秀昆,曾前往7省上百家医院和急救中心调研“黑救护车”问题。他发现,黑救护车太普遍了,病人和家属很难分辨。
黑救护车的踪迹并不隐蔽,很多就堂而皇之地停在医院门口,甚至停到医院病房大楼前,联系方式搁在驾驶室,或者人就守在那,等着人搭讪时揽活。
“有的病人要转运,不咨询120,也不问医院,看到医院门口停了救护车,上去咨询一拍即合。”武秀昆发现,黑救护车尤其集中地盘踞在三甲医院及其周边。
倪辰是某超一线城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简公益”急救志愿教官,她告诉南风窗,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些挂着外地车牌的救护车,其实和社会车辆一样,是付了停车费才停在医院里的,和医院没有关系。“在我们这,除了印有‘××(城市名)急救’,小程序可查询的,其他一律视为黑救护车,很多医院急诊也不让它们进,哪怕有的确实是外地正规的救护车。”
多位急救人士告诉南风窗,外地牌照是辨别“黑救护车”的一个标识。
“你到北京一看,大医院周边有挂河北牌照的、有挂山西或者内蒙古牌照的(救护车),不排除有一些是这些省地把重病患者送到北京来救治,但相当一部分是黑救护车。”武秀昆对南风窗解释,它们之所以挂外地牌照,是因为救护车属于特种车辆,向交管部门申请牌照时,要有医疗机构提供手续,车辆才能用于医疗服务。
在医疗条件更好的城市,要给救护车挂本地牌照门槛高,资质审核严。“本地大医院挂靠不上,很多人就到外面想办法,靠关系找外地的小医院,给救护车挂了牌,然后开到这些地方来。”
即便救护车上了牌,也不能摆脱“黑救护车”的嫌疑。
调查“黑救护车”时,武秀昆会看车上配备了哪些医疗设备,随行医护有没有执业资质。有回他就逮着一辆可疑的救护车上前问:“我的病人心脏不太好,想用监护仪,你们有没有?”
对方说“有”,紧接着,武秀昆提出想打开看看,对方鼓捣半天也打不开,他推测“它要么坏了,要么长期不用蓄电池没电了”。
下一分钟,他又问起跟车医生。半小时后,来了个穿白大褂的人,没问上几句,对方就露馅儿了,“他压根就不是医生”。
武秀昆告诉南风窗,黑救护车条件简陋,有的只有担架和氧气袋,一些基础设备甚至使用陈旧报废品,或压根不能正常使用,且绝大多数没有医护人员随行,或随车医护没有执业资质又或能力不匹配,提供不了可靠的医疗服务。
“黑救护车的核心,是低成本投入和低成本运营。”武秀昆说,而收费不公开不透明,或漫天要价,或低价揽活中途加价,也是普遍套路。
但这些漠视生命的黑救护车不仅就近停靠在医院,还以小广告、小卡片的方式,渗透到医院门诊大楼和住院部,出现在科室、病房、茶水间、卫生间里。“(当年调研时)黑救护车的小卡片、小广告,我们就收集了两箱。”
为了招揽生意,黑救护车还会在医院开拓人脉介绍生意。虽然医务人员极少介入其中,但保洁和保安却很容易成为介绍人。
鱼目混珠的黑救护车,就这样出现在病人和家属面前。
一位医疗转运从业者颇感无奈:“普通人对医疗转运不是很了解,一看到救护车,都以为是120。”
医院的救护车去哪儿了?
尽管有诸多风险隐患,但不少人却对黑救护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倪辰告诉南风窗,只要不发生意外和纠纷,其实很多人并不会投诉黑救护车,“甚至家属也很感谢黑救护车,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她举了个例子:“老人骨折或者生病卧床,想回湖北老家,你打120,救护车不送外地怎么办?外地老人或者其他异常情况去世,想落叶归根,把遗体送回东北老家怎么办?正规120就是不能办,不能送。但这是真实存在的需求,有经济、伦理、文化方面的因素。”
倪辰进一步解释,包括家属“自行要求”从基层医院向上级医院转院的需求在内,医院和急救中心大都无法提供救护车转运,因为这些救护车是“就近救急”,一般只负责方圆10公里距离内的急救服务,救护车和人员的数量一般按辖区人口数量配备,服务辖区内市民。
“如果为此单独抽出一组人和一辆车出长途任务,那本辖区的急救服务就会有缺口。单独配备出长途的车和人,又需要投入更多财力人力且收支极其不平衡。”倪辰说。
更何况,急救资源本就紧张,现有用于急救的救护车,约八成的紧急呼叫,是被手指割伤、睡不着觉、便秘、喝醉酒闹事等一些非紧急情况占用。
武秀昆曾参与起草《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当中有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之所以如此划分界限,既是为了避免有限的急救资源进一步被挤占,也受制于财政经费紧张、医护人手不足。
干了26年急救中心主任,武秀昆太清楚急救在人手上的痛点。
“医生不愿意做院前急救,不愿意上救护车,不愿来急救中心,来了以后就想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武秀昆解释道,因为急救医生偏向于全科医生,专业性比不过专科医生,服务短平快。到了现场,做完急救处理,就转交给其他专科医生了,“人连个脸都还没混熟就走了”,病例、手术、科研数据都是别人的。急救人员的待遇,从收入到评职称再到晋升,都矮人一截。
既然人手连急救都无法保证,转运更顾不上了。
有限资源当中,其实也有一些院方及其合作方的救护车,专门干着转运工作。
在特定的综合性医院的某个区域,会有救护车把下级基层医院诊治不了的疑难危重病人接上来,或者患者病情稳定了,再送回基层医院。但这个转运只限于“医联体”“医共体”的范畴,也不是每个医院都有救护车可供转运。从覆盖范围来看,医联体和医共体在县域和市域。
尤其那些跨省求医的病人,还是免不了自己找转运车。他们当中不乏危急重病患者,可究竟由谁来承担这一群体的转运,缺乏明确的规定。
多份医学文献表明,即便是在医院内,转运危急重病患者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都很高,院际转运的风险更大,转运时,对救护车设备和医护配置的要求也更严苛,医院同样人手紧张,难以协调。
归根结底,“黑救护车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主要是患者合理的转运需求,在正规渠道得不到满足”,武秀昆说。
正因为病人难以向医院寻求长途医疗转运服务,倘若病人状况相对稳定,黑救护车有时的确能帮上忙,提供一个比普通社会车辆更宽敞的平躺空间。
然而风险在于,那些“结束或放弃治疗就回家”的需求,和“病人转院继续治疗”的需求同时存在,连同危急重症患者的转诊需求,黑救护车有时不加区分,照单全收,随时可能失控。
“无底线”挤压市场
干了10年医疗转运,陈仲仁见过黑救护车最无序的样子。
有的司机买来二手面包车,简单改装成能躺人、可以上担架的样式。至于揽活,一靠关系,二看谁的拳头大,“早前在医院里面经常是打出来的”。有的是家庭式经营,丈夫当司机,老婆充当护士,儿子学点医学常识,披个白大褂充作医生,“一家三口买台车就干了”。
用市场的办法对付黑救护车问题,广东的探索走在了前面,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15年,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成立,经广东省卫健委批准,在全国率先试点探索“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也是目前为数不多有省级卫健部门资质证明的民营医疗转运机构。
陈仲仁是公司现任总经理,他告诉南风窗,原先省机场集团下面有个民航医院,做的是机场(医疗)保障,有现成的医生护士和急救车辆。省里发现既然有转运刚需,黑救护车光堵也不行,还是要疏通,民航医院承接了试点。
此后,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999、长三角地区城市也开始试点“非急救医疗转运”,对医疗转运服务加以规范。
武秀昆对南风窗解释,同样以救护车为交通工具和工作平台,120的救护车负责“院前急救”,以现场抢救和途中监护治疗为主,而“非急救医疗转运”以患者转运护送为主,交通工具还可以是高铁和飞机,服务范围可以出市出省出国。现实中,有能力的转运机构也参与执行重症患者转运的任务。
“真正做好这个行业是很难的。”陈仲仁说,尤其2020年后,救护车数量大增,眼下的低价竞争,让他有种“争不过黑救护车”的沮丧。
他测算过成本,如果收费低于12元/公里,都没办法保证运营。场地、年审、养护80多辆车和设备、上百号医护担架员都是固定支出,一台ECMO,国产化了也要七八十万,会操作呼吸机、ECMO的医生,有的医院甚至找不出一两个。
可那些没有资质、低成本运营的黑救护车,已经喊到五六元/公里,按最低成本出价,靠上车后中途加价赚钱。“我们不能这么干……医疗转运不是打的士,送到地方就拍屁股走人了。得把病人的情况了解清楚,再转到车上,也给下一个交接的医生讲清楚。风险不能把控,责任谁也担不起。”陈仲仁说。
即便守住底线,许多合规机构不得不低于报备公示的收费标准报价。以黑救护车为竞争对手,是必须面对的现实。“监管力度不够,我们只能靠自己跟黑车竞争……说难听点,现在能够维持运营就很不错了。”
收支压力大的并非个例。据武秀昆了解,国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北京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999,收费标准远低于平均水平,也有“出车越多,赔钱越多”的两难。
倪辰理解民营医疗转运从业者的难处,有政府补贴的120救护车,基本在亏损,更别说那些没有政府补贴的民营转运救护车。“要求别人提升规范性和专业性的前提,是要考虑资金支持,要让专业的有价值,规范的有回报。”
武秀昆认为,我们要拿出更负责任的态度:“非急救医疗转运不是做慈善,如果它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最后倒霉的是普通人。”
破与立
采访中,同一个问题反复出现:谁来监管黑救护车?
“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被解决。”武秀昆说,原则通常是谁审批谁监管,但是,那些光套牌没办手续、连审批责任人都没有的黑救护车,监管无从下手。
即便明确了监管责任人,实际操作仍有痛点。陈仲仁曾询问过执法单位,他们的两难在于:黑救护车上路转运病人的时候,怕耽误病情不敢查;空车停在医院停车场的时候,没有执法依据,因为停车不违法。
在苏州,当地在“非急救医疗转运”的经验总结性论文里也不讳言:尽管当地卫健委在全市医疗机构院内和入口部署,只有正规非急救转运车辆才能进去,仍有“黑车”能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医院里面去接病人,并时常有劫单情况,甚至黑车购买套牌车,私自安装警灯警报冒充“120”。
现有处罚力度也难以震慑。对于违规改造外观的车辆,交警仅能处以200元罚款;对于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交通运输部门存在取证困难问题。外市正规救护车来苏州开展营运业务,没有处罚手段,只能给外市正规救护车所属的急救中心发函,协助召回车辆回原属地。
即便有诸多难处,但宽松的监管终究放任黑救护车成为诡异而危险的“强力”乃至“主力”,不仅挤压合规机构的生存空间,更酿成事故、威胁转运病人的生命健康,连累急救体系背锅,挫伤医患信任。
多年来,武秀昆调研、撰文、写书,为“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鼓与呼,视其为整治黑救护车乱象、维护医疗秩序的一个解法。
“不破不立。我们需要覆盖全国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体系,建好了,黑救护车自然销声匿迹。抓两头带中间,打击黑救护车,提高其违法成本,也肯定类似北京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999这样的先进典型,再把中间人给带动起来,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中国的县级行政区划超过2800个,在他的设想里,每个区县都该至少有一个非急救医疗转运机构,而他援引一项调研数据称,到2023年中,非急救医疗转运机构数量只有659个。他担心,这两年的数量更少了。
眼下,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仍在播种试点阶段,整体力量仍显薄弱,标准和分工尚不明确。从659到2800乃至更多,前路依然漫长。
等待这个数字壮大的每一个日夜里,在更多规范普惠的救护车走向转运病人之前,黑救护车仍环伺医院,等待下一个目标。而在城郊、农村、基层医院,如果病人最终上了一辆黑救护车,只是因为他们没得选,而他们仍想赌一个生机。
(文中倪辰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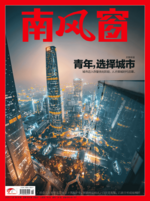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