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一座“爱乐之城”的诞生
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再只看经济体量,其松弛的气质与质朴的生命力,也深深地牵绊着有梦想的年轻人。

2024年9月6日,贵州贵阳,张国勇指挥贵阳交响乐团演出交响组曲《多彩和鸣》(图/视觉中国)
中国的爱乐之城在哪里?
恐怕是一个你未曾想过的地方——贵阳。
8月盛夏,黔中腹地贵阳的气温只有20℃出头,傍晚七点半,天光未暗,晚风微凉,距离南明湖一公里的贵阳大剧院准时躁动起来。
一支名为《风与鸟的密语》的乐曲开始演奏,音乐厅内座无虚席,演奏台上,除了乐器,手机、响指、敲击也轮番上阵。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的64名乐手,也仿佛化为了旋律的一部分,在席间的轻呼与惊叹之下,完成了一场古典乐的现代化演奏。
贵阳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张国勇走上台,朝坐满三层楼的观众深深鞠了一躬:8月22日,贵阳交响乐团将首次赴欧洲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意大利三国演出——他们是此行受邀参与的唯一的中国民营乐团。
浓烈的艺术氛围之下,人们止不住发出感叹:竟然是贵阳,为什么是贵阳?
事实上,今年以来,这组疑问早就在互联网疯狂生长。各种信息都显示,贵阳,早已不再是那个低调的山区省会、避暑之都。
2024年,苏杭成渝接连站上风口,但真正超越深圳,站上全国人口增量第一城的,却是贵阳。此外,贵阳也是实打实的“年轻之城”,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1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5.4%。
再回头来看,交响乐这一看似“高冷”的音乐品类,能在贵阳落地生根,并在业内声誉卓著,也就并非偶然了。或者说,其实贵阳低调生长的真正秘诀,就藏在交响乐曲之中。
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再紧紧围绕经济体量、产业发达程度,其自身气质的松弛程度、包容程度与质朴的生命力,也成为年轻人关注的因素。
贵阳交响乐团(以下简称“贵交”),就是窥见这座爱乐之城生长脉络的一个窗口。
2009年,企业家黄志明与王小星夫妇在贵阳创立了全国首支由民营资本独立注资的职业交响乐团,开创了中国“政府支持、企业出资”的“民办公协”交响乐模式。这一动作,也填补了整个西南地区职业交响乐团的空白。
16年来,贵交吸引了陈佐湟、刘云志、李心草、里科·萨卡尼、张国勇等海内外音乐大师先后加盟。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聚集在中国西南腹地,组成了一支真正的国际化乐团。它随时敞开客厅,以低至百元均价的门票,邀请市民随时前来做客。
16年,16个音乐季,700余场音乐会,贵交吸收了黔地的生猛与爽朗,音符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向世界眺望。贵阳市作协副主席杨骊曾在长篇报告文学《一座城市的交响》中这样描述:“一个关于城市与音乐的梦想,经过一群人的不懈努力,落地生根,由小苗终长成参天大树,花繁叶茂。”
贵交逐步成长壮大的过程,不仅是一群音乐人带着一种品味和艺术走出群山的过程,也是贵阳这座城市逐渐被当代看见的过程。
山城的,世界的
乐团的中提琴副首席魏杰是个“85后”哈尔滨姑娘。2009年,魏杰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后,在北京通过一场招聘加入了贵交,成为乐团的第一批成员,也是真正意义上“被贵交培养出来的”乐手。
自2009年成立以来,乐团持续实施聘用制,乐队人员是流动的。如今,与魏杰当年一起加入乐团的成员,还剩下不到20位。
“因为我们不吃大锅饭,所以对乐手的专业素养有很高要求”,这是魏杰享受的一种“生命力”状态,使得乐手们把音乐放在第一位。这些年,魏杰见证着乐团源源不断流进新鲜血液,这也会给她带来激情和挑战,“不会让你觉着这个工作就是稳的”。
她的搭档,中提琴首席叶卡尔是捷克人,他常常在排演时直接当众提出自己对某一个微小旋律或节奏的不同看法,希望和指挥商量调整修改。“其实不改,外行人也分辨不出来”,但乐团里不乏叶卡尔这样,不受“中国人的职场规则”规训,仅从音乐角度完成每一场演奏的人。
长笛声部首席梦伊,一个29岁的广西女孩,是2022年进入交响乐团的,时逢疫情,乐团的排演和正式演出都搁置了两个多月。次年解封后的第一场排演,吹的是拉威尔的作品,乐队伙伴里有人还没康复,但士气丝毫没受影响,“所有人都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三年后,这份毋需言明的凝聚力在欧洲再现。乐团巡演的第一场在卢布尔雅那,当地时间晚上8时,约为北京时间的凌晨3时,每个人都没有倒过来时差,中场休息的时候,梦伊看见张国勇眼里血丝未散,但开场后,“所有人立刻精神抖擞,丝毫看不出倦意”。
贵交的成员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签”。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毕业于不同的学校。贵交2025年8月的一份招聘写道,各岗位所需人才都“不论国籍、不限性别”,演奏员的起薪为税前1万元/月。与之相对应的是,2024年,贵阳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5万余元,折合下来约4000元/月。
高薪之下,是乐团几乎每周都有演出。成员们每天都会一起排演和训练。譬如,欧洲巡演前夕,在贵阳的这场演出,乐手们为之排练了将近一个月。
这场演出也将被贵交带出国门。为了在世界留下更多中国元素,总指挥张国勇特地脱下穿了8年的燕尾服,专门定制了一套中式正装。
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贵阳的热情不比国际市场低。一场安排在周一晚上的音乐会,开演前一周,票就售罄了。
贵阳人擅长享受生活,周一和周五,心态上或许没有太大不同。
当然,更直接的原因,也许是票价亲民。自2009年成立以来,贵交的定价平均不超过100元。而在全国范围内,一场交响乐演出的票价,通常在100元至800元不等。后者也符合人们的“刻板印象”,即交响乐通常是大城市里有钱人的“专属”。
留住观众,开拓自己的观众,用自己的办法让古典乐融入山城,贵交有自己的办法。
“少一点麻将声”
贵阳交响乐团的起源,要从一家百货公司说起。
1995年,贵阳本地人黄志明与一行志同道合者,到发达城市研究考察后,回到家乡创办了贵阳首家时尚百货公司,就是如今坐落于市中心地段的星力百货。它是贵阳全城第一家百货大楼,也是第一个打破传统零售业模式,引入新型现代公司制度的百货公司。
黄志明是“60后”,商人身份之外,还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
人由他所处的环境塑造,但一些人会反过来想要重塑环境。虽然乘着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之风投身商海,但黄志明内心深处一直有“搞音乐”的念头,他拿着开百货公司赚到的钱,坐着飞机满世界找音乐会听。
20世纪末,贵阳的“文艺市场”几乎没有起步。经济发展让居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但百姓最熟悉的日常文娱项目,还是打麻将。
相较于其他历史长的城市,贵阳谈不上太多文化底蕴和艺术积淀。“古典”二字,更是天然与贵阳不搭。黄志明认为,即便通过多年的修路、建房,当地生活条件改善,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依然匮乏。
他曾在采访里说:“更多的人把时间浪费在打麻将或者去网吧,很多年轻人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这真的让人很遗憾。”
他想带头改变这一切,既作为一个贵阳市民,也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拥趸。
有什么办法可以既最大程度保有音乐的创作自由,又能为百姓提供一个长期存在的、稳定的音乐欣赏空间呢?
已经有了第一桶金的黄志明,思考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叫上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友与音乐人,自己出资,政府为辅,创办一个民营的交响乐团。
当时,整个中国古典音乐市场都是政府主导,交响乐团也通常是由政府出资或以政府出资为主,吸引一部分民营资本。
贵交筹备建团的那段时间,每一步都朝着未知的方向探索。一天深夜,黄志明与后来的乐团名誉团长刘云志一起探讨乐团发展,直到次日凌晨4时,两个人来到附近一家牛肉粉店,吃了两碗不知算是夜宵还是早餐的粉。困顿与黎明的交错中,黄志明对刘志云说:“就算我不在了,这个乐团也要照样办下去!”
黄志明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这个城市里面想听音乐的人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让艺术家有尊严地在贵阳生活”。
2009年2月19日,在贵阳市的支持下,黄志明和王小星夫妇创立了全市第一家交响乐团,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民营交响乐团。贵阳也从此成为首个开创“政府支持、企业出资”这一交响乐团存在机制的城市。
彼时,黄志明已53岁,但仍然不甘就这么“安享天年”。他决定每年投资1000万元作为乐团运作经费。“我早已想好最坏的情况——以后每年支出1000万。赚回一点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
贵交的发展速度出乎意料。
乐团成立半年后,就迎来了第一场正式音乐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暨贵阳交响乐团成立首演——向祖国献礼”。随后,2010年,贵阳交响乐团经中央电视台特邀,录制了新年音乐会。
2016年9月29日,受邀参加韩国龟尾国际音乐节的贵阳交响乐团,在听众的热情邀请下,乐团指挥三次上台谢幕,临时安排加演。当时,龟尾市市长南洧镇一行称赞贵阳交响乐团是“真正的国际一流的交响乐团”。
7年后的夏天,在奥地利的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全场观众同样纷纷起立鼓掌。一位观众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听说这支乐团来自中国西南部,那里有很多山,是吗?那和这里很像,奥地利也有很多山。”
一个来自西南山城的乐队,真正意义上地走出去了。
爱乐之城的炼成
十余年来,贵交见证了乐团从个位数成员到上百人,也见证了贵阳听众对古典乐从陌生到熟悉的过渡。
乐团刚成立时,不少捧场的观众都是黄志明的亲朋好友,或是星力集团内部的员工。由于不懂演出时的乐章间隔,一些听众会随心所欲地鼓掌、叫好。
于是,黄志明找来两个集团内部的员工,做了两个提示牌,在每个乐章间隔举着牌子走到观众席两侧,示意什么时候应该鼓掌、什么时候不应该鼓掌。几年后,举牌变成了舞台两侧的两个LED屏,专门有人在后台操作“请不要鼓掌”“请鼓掌”。
当时,听众的积极配合,带有一种形式上配合的朴素热情,“但一两年后,这个形式就不需要了”。乐团的员工表示,越来越多真正的乐迷出现,而一场演奏会,只要有一两个懂得节奏与喝彩的观众,其余的就会被带动起来。
贵阳作家袁政谦曾撰文回忆在2010年听贵交演出的经历:“我注意到,这两场音乐会的听众都表现得非常热情,并且秩序良好。只是有些听众还不很熟悉古典音乐会的‘规矩’,有些逾矩的表现(如乐章结束后鼓掌;如乐曲刚一完结就高声叫好),说明听众也有一个培养的过程。”
“95后”音乐学者胡瑞雪是贵阳人,离开家上大学之前,去听贵交演出的习惯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初高中时光。贵阳的交通不算很便利,他常常从家中搭老式公交,坐一个半小时去大剧院,“人多的时候就后门上车,前门补票”。但音乐会的每一张票根,胡瑞雪都保存了下来,至今已有好几十张。那些年,贵交的学生票是10元一张,后来涨价了也不过才15元。
当时的总指挥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音乐艺术博士”陈佐湟,胡瑞雪明显感受到,有他在的时候,演奏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高很多。即便不是每个听众都懂艺术,现场也有不少人热泪盈眶,“艺术真正展现的是你(表演者)内心的表达和情绪”。后来,胡瑞雪在音乐领域一路求学,读到博士,他渐渐意识到,虽然古典乐“相对挑剔观众”,但随着乐理科普与演奏形式的创新,它终究还是有朝着大众文化接洽的趋势。
音乐是感染力的艺术,它穿透语言、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人们连接起来。
2024年,乐团成立15周年庆时,他们收到了一封乐迷来信。那是一位年龄较大的医生,自称从贵交建团开始就坚持听演出。后来,他的子女又告诉乐团,这位医生,也是一个癌症患者,但每次去听音乐会,都会非常有仪式感地把自己捯饬妥帖。
对任何一种艺术而言,欣赏和感受都没有语言和专业门槛。因此,要进入一场好的音乐会,未必需要审美作为入场券,就像登一艘船,买了票,放松身心,跟随船长和水手,尽情感受风与浪的拥抱便是。
贵交的双簧管演奏员李想向南风窗解释,双簧管的功能之一,就是辅助整个声部变得立体,将音乐从单一旋律纵向拉升。因此,他不直接承担“旋律性”的工作,但让交响乐变成一种每个人都能置身其中的体验。
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与流溢,倒像是贵阳这座城市多年来不断融合、吸收与自我调适的过程。
与平原、沿海地区相比,拥有山地和高原阻隔的西南地区,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上都是相对粗粝的、乡土的。可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交响乐是优雅的。
时至今日,山城贵阳仍保有着原生的张扬、野性与泼辣。充斥市井的酸辣火锅和油滋味儿,“地无三尺平”的崎岖,十八弯的陡峻,城市里不掩破旧的建筑、慵懒无章的道路和无处不在的坡道和洞穴,当地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法则,似乎天然站在精致的反面。
但“不讲究”的另一面,是松弛和无拘束。贵州从先天恶劣的地势里走出来,虽然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桥梁,但自认人难胜天的贵州人,从这份世代相传的豁达里沉淀出来的,是一份敢于享受的自得。
如今,黄志明定下的一些原则,依然被贵交乐团坚守着,比如从不轻易接商演。而可接和不可接之间的界限与标准,则是“每位音乐家只要站上台演出,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乐团宣传杨玲告诉南风窗,像“房地产开盘”之类的活动邀请,他们就不会接。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变与不变之中,有扬有弃,才能张弛有度。
某种程度上,一个乐团就是一座城的河流,是用动态音符谱写的当代史。如今,曾长年被遗忘在大山深处的贵阳,正变成旅游热门地,来来去去的人潮,和也许终有一天会变得雷同的商业项目,都在不断制造一个新的贵阳。但因为有贵交这样的河流存在,这座城市也将保有最原始而纯粹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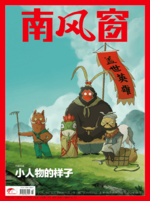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