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医生降薪
我们都希望医疗更公平、更轻负,但真正让它走向良性的方式,不是减少医生的收入,而是保障医生的尊严,让他们可以不必为生计焦虑。
前不久,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医生薪酬下降的报道,读者们都很关注。
在后台收到的留言中,很多人表达了对医生工作的理解,以及对确保医生合理收入的希望。但同时,也有一些不同声音,还比较刺耳。
“早该降了,就算降了还是比普通上班人要高。”
“过去高检查费、高医药费拿惯了,如今不合理收入减少了,觉得不习惯了。”
这篇报道的初心,是想让公众看到在当前仍待完善的薪酬制度下,医生面临的职业压力与困境乃至由此产生一系列反应。不过,有一部分读者把它解读成了“医生挣得太多”的故事。浏览了这些评论之后,我理解了在采访过程中被诸多医生拒绝的情况,舆论的复杂在让所有人都变得异常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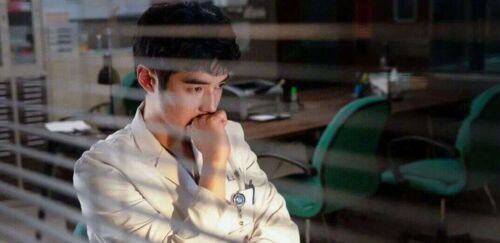
《问心》剧照
同时,这也再次表明,在医生和病人之间,不光有信息差,还有信任差。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医疗是一生中最沉重的支出之一。看一次病,住一次院,挂号、检查、化验、治疗……随随便便几百几千元就没了。
因为公众多跟医护接触,不知晓医院的收入模式和医生的薪酬制度,所以他们把这种医疗负担和医生收入的“高低”联系在一起,其实并不奇怪。
但问题在于,医生的“高收入”,并不是他们自己随意拔高的结果,而更多是历史的产物。
在我们的采访中,几乎所有医生都提到,他们的收入和医院营收紧紧捆在一起,固定工资只占一小部分,绩效工资才是“大头”。而绩效的计算方式,往往与医生的“创收”挂钩,做的检查越多,开的药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医生绩效也越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这种固化的薪酬逻辑支配了绝大多数医院和医生。
这些年,国家的医疗与医保改革不断推进,“以药养医”“过度检查”等旧的盈利模式被逐步清除。但按照受访医生们的说法,问题在于在政策持续调整的过程中,新薪酬体系仍在逐步完善中。
目前,医生的收入依然与“创收”挂钩,只是“创收”的空间跟以往相比变小了。以往存在的一些不规范做法得到有效规范,但新的激励机制仍在探索之中。

《问心》剧照
一位受访医生说,作为医生,他们也想靠自己的医疗技术挣钱,而非多开药、多检查。但现在这个薪酬体系下,固定工资比例太小,一旦医院营收下滑,绩效就随之下降,收入减少。
很多留言都在说,其他行业也在降薪,医生降薪有什么大惊小怪之处,何况他们收入本就高,降了也差不到哪里去。
或许大家的理解是,发给医生的钱少了,人们看病的负担就会轻一些。但情况真是如此吗?
至少目前来看,医生降薪后,并不意味着医疗负担减少,因为“节约”的那部分钱,并不会直接回到患者手里。
而且,如果降薪削弱了医生的积极性,甚至让优秀医生离开,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疗服务的稳定性。
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医生的高薪并不是例外。如英国受薪专科医生收入约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3倍,瑞典为2.2倍,加拿大为3倍。
原因很简单:
一是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是以人的“健康”作为最终的产出,而“健康”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最基础条件,一切都建立在其之上,这决定了医疗服务的高价值;
二是培养一名医生的成本很高。一名医生在执业前,最起码要经历5年院校培养、1-3年住院医师培训、2-5年专科医师培训,全程周期大多在10-13年左右。
简单来说,其他专业学生大学四年毕业后就可以工作,但医学生最少需要七八年时间才可以真正就业。所以,医生的前期投入大,培养成本高,就业后薪酬自然相对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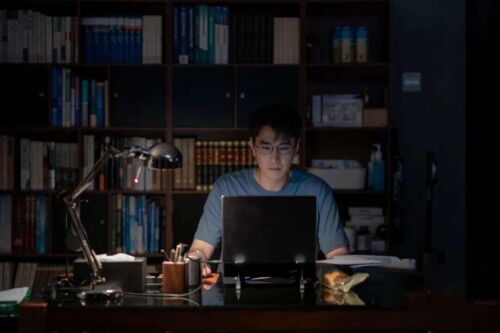
《问心》剧照
公众的情绪也应该被理解。毕竟,医疗是和每个人钱包最直接相关的领域。可如果我们只把医生降薪看成“伸张正义”,可能就忽略了一个更深的问题:
当医生没有稳定收入保障时,他们是否还能专心去救人?
医生的“高薪”从来不是特权,而是对他们的专业、责任和时间成本的回报。因此,合理的制度,应该让他们靠技术吃饭,而不是靠创收养活自己。
我们都希望医疗更公平、更轻负,但真正让它走向良性的方式,不是减少医生的收入,而是保障医生的尊严,让他们可以不必为生计焦虑。让医生能够专注于医疗本身。
那样,医生才能专心治病,病人也才能真正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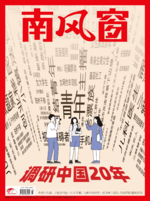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