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取法时代
“我不会说这个学者提出了一套宏大的思想,或者做了一个经典式的研究,但是,如果要了解当下这个时代,恐怕以后的人会说,你可以读读许纪霖当时的研究。”

许纪霖形象(摄影/南风窗郭嘉亮)
即将年满69岁,近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许纪霖仍很忙。他在2025年有两本引发关注的新书,一本《前浪后浪》,是他自陈2010年代后,以“精神史”分析的方法,回到知识分子研究的心血之作;一本《狐狸与刺猬》,虽是旧书再版,但置换了60%的篇目,跟紧了我们所在的时代。
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许纪霖的全盛时代,属于知识分子的C位早已不再,宏大叙事的光束移开,讨论的场域也变了:更多人转向日常生活的叙事,公共空间里可供反复推敲的“文本”越来越少。
许纪霖并不劝人“怀念好时光”。在他看来,时代的好坏不由个人选择,但个人仍要对自己的所为负责——因为一个人的选择会凝结为他自己的命运,也会以细小的方式沉入历史。
所谓“垃圾时间”,也许只是我们拒绝放弃的那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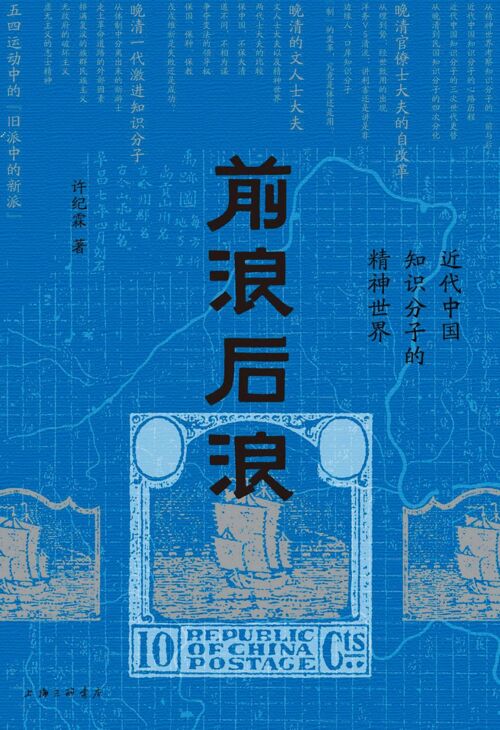
《狐狸与刺猬》《前浪后浪》 许纪霖 著
命运总是被安排
许纪霖谈自己时,话题总是一次又一次被拉回大学时代。2000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踏进华东师范大学时的自己,那是1978年初,“可以说,心灵底处,还是一张有待描画的白纸”。
但是那年的他,已经21岁。
成长于上海,许纪霖十多岁时的少年时光,正是中国剧变的时期,他在动荡中求学,也曾下乡三年,心灵怎么会是一张白纸?
“人的痛苦是因为他有选择权。”许纪霖语气平淡地说道,现在人的焦虑,也在于他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命运,因此才会彷徨和焦虑,“命运被决定的时候,(人的)心态是安之若素的”。
中学时期,许纪霖算是学霸,“门门100分”毫不费劲。当时,上海有政策规定,一个家中已经有一个孩子留在上海的,其他孩子就必须去农村。许纪霖的姐姐留在了上海,因此他必须下乡,“书读得好不好,和你的未来没有关系”。
好在,少年许纪霖喜欢读书,纯粹把它当个爱好。
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里订的《解放日报》,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喜欢看。8岁那年,家里的书被全部抄走,但社区里的知识分子家庭多,有的邻居还有藏书,《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偷偷地流行,于是大家伙儿传着看。
对于特殊的年代,许纪霖并没有太多阴影郁积。相反,家里没有大人,“死的死,走的走”,小孩子有了充足的自由,竟有些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主角。只不过电影拍的是北京“大院子弟”,这一边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
1975年,中学毕业后,仍然懵懂的许纪霖,“稀里糊涂地下了乡”,去到上海郊区的南汇县东海农场。
下乡时期,许纪霖记得的最辛苦的事,是每年冬天去围海造田。一群人把河泥挖出来,人力担着去填海,“来了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说了一句豪言壮语,说是填海一直填到东京去”。十几岁的人,挑着比自己还重的两袋河泥走几十米路,几天下来,“我就觉得是漫无尽头的苦难”。
但许纪霖自称是幸运的。下乡后,他“写点小文章的小才华”显露出来,他被调到连队的宣传组,顺便也管图书。借着“采购图书”的方便,他又开始读书,尤其对苏联“解冻文学”印象深刻。那些没有教条的小说,关于复杂人性与对爱的追求的文学,冲击着他。
在农村里的青春岁月,他和很多人一样想要回城,但那也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像流星一样乍现,又在黑暗中沉寂。
许纪霖说,人没有选择的时候,就只是活着。这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无喜无悲。
因此1977年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耳朵时,许纪霖正从重庆返回上海,出峡谷正好看到一片辽阔的江面,“突然自己的前途也豁然开朗”。
他回忆说:“像我这代人,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绑在一起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国天下情怀也是这么来的。”
1980年代的“新范式”
个人遇上大时代的序幕开启,无疑是幸运的,但又难免美中不足。
经过三四个月的准备,下乡青年许纪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但他心仪的是中文系,心中有个“文学梦”,最终录取他的却是政治教育系。他也只能接受。
“我说命运,实际上是被安排的。”回忆中,许纪霖突然谈起命运。“即使被安排了命运,依然有自己可以选择的空间,去表现的空间。”他说。
大一时,“文学梦”未死,许纪霖写了一出话剧,没想到还打败中文系同学,拿了全校第一,后来代表华东师大参加了上海的汇演。许纪霖笑道,这为系里争了光,自己也有了“才子”身份。
读到大三分专业,因为“哲学太抽象,又没有经济头脑”,许纪霖选择了系里的政治专业。
命运的齿轮转动时,其实悄无声息。许纪霖的课题,从中国民主党派研究开始,但或许是“文学青年”的特质作祟,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大部分成员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纪霖的兴趣,引导着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范式。
不过,大三学生许纪霖,距离学术圈还很远。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以他的年纪,一般要分配到外地。但在大学期间,他被抽中拍摄“思想教育电视片”,要去瑞金、遵义、井冈山等地取材,到了毕业,片子还没拍完,“就稀里糊涂留下了”。
后来许纪霖才清楚,“好运”背后,不光是运气。当时一家上海的报社,看中了学校里的“才子许纪霖”,点名要他。即便没有留校,他也会留在上海。
当然,1982年留校时,25岁的许纪霖,对命运的草蛇灰线一无所知。他仍然在坐冷板凳,“起初什么也不是”,后来成为小助教,再后来申请成为讲师……
从大学的最底层做起,许纪霖的感受是自由,没有人约束他的知识分子研究,“没人指导,也没人要求,就一头扎在图书馆里”。
1987年,两篇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陆续发表,文章视角新鲜,内容独特,一脱以往框架叙事的窠臼;同时,文章踩中1980年代“文化热”中人们的关切,一时反响热烈。许纪霖声名大噪。
现在回忆“年少成名”,许纪霖念怀的一点却是,因为他的“文学梦”视鲁迅为偶像,模仿了文笔,因此“文章像是60多岁老头写的,其实那时候不过30岁而已”,许纪霖笑道。
“最好的日子”
被许多人所怀念的1980年代,对许纪霖来说,最难得的是在公共空间自由表达的风气。
“今天的一切都KPI化,大学里也有一套标准和制度来要求每个人,于是人异化了,来适应这套KPI,会很理性地设计自己。”许纪霖说。但他是一个感觉主义的人,80年代的他,不过秉持“以人为中心”的想法,凭着文青的特色,就开始做知识分子研究。
哲学家梁漱溟曾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问题中人。”这句话正中许纪霖内心。“我也是内心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去做研究”,由自身出发地研究知识分子的命运,再从中看见自己,正好赶上了“文化热”的时代。
新旧交替之际,许纪霖开始游走于学术界与思想界。年轻人躬逢其盛,自然踌躇满志,但冷峻的现实与漫长的考验,也会来临。
1990年代,许纪霖开始省察,“我的研究是没有家法的,有点野路子,是自己闯出来的”。渐渐地,“心态史”的研究视角,无法满足他,“就慢慢开始转向思想史研究”。
这个时期,他受到历史学家张灏先生的启发,把这套方法归结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实验性研究”——提出问题,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研究。
研究阶段的转换,给他很深的体会:“当某个专业做不出新的东西了,不要急于钻牛角尖,你暂时放下,跳出来、拉开视角,做一个更大的背景研究,这时再回去,你可能就有新的发现。”
因此在许纪霖笔下,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生态,开始有了更复杂的图景。传统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分野被打破。“我们不要以为三派人相互之间没有共享的那部分,共享的那些东西,就是更深层的东西。”由此出发,他开始深入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核心观念分析。
这时期的写作,后来大体收进了两本书里,一本是2011年出版的《启蒙如何起死回生》,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家国天下》。
学术硬功夫,难免十年磨一剑。新世纪以来,外部环境迅速变化。
许纪霖承继1980年代的传统,“永远两条腿走路”——“我不会因为参加公共思想界而放弃研究,也不会因为研究就放弃公共思想界”。
他最怀念的是网络BBS时代,思潮涌动,各方激辩,但都以说理为主。“说理”很重要,许纪霖认为,只有BBS论坛相对平等的发言权,以及足够多的表达版面,才会包容当年的思想激荡。在这一形式下,知识分子有地方“说理”,还能站在主流位置。
但BBS衰落后,碎片化时代到来,属于知识分子的空间就似乎逐渐萎缩了。

许纪霖在2025南风窗社会价值年度盛典现场(摄影/南风窗郭嘉亮)
时代中人
公共知识分子的“退场”,在许纪霖看来,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致。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越来越局部化、专业化、学院化,同社会的关系日趋淡薄,越来越分离。这个群体赖以生存的“公共性”逐渐减弱。
如果不面对知识分子内部存在的问题,将一切责任推给环境,以为环境发生某种变化就可以回到昔日荣光,那么或许,公共知识分子的退场就不可逆了。这是许纪霖所担心的。
从更大的尺度来看,知识分子其实是自己的掘墓人:他们曾经掌握话语权,设计了网络民主的环境,待到这个环境成为现实,消解了话语权,他们反而不再被需要。
许纪霖提到,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学生也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是屠格涅夫所说的“多余的人”。
他并不是没有挣扎。“2016年到2020年左右的时间,很艰难,时代变了,你明显感觉到自己被挤到边缘了,你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呢?”他也曾这样内心焦灼。
数十年的研究,让他对这100多年几代知识分子的起起落落,了如指掌,他也因此更加明白,变化是不可抵挡的。
就像白话文运动开启以后,“你要进入公共空间,你就必须用大众所喜欢的白话文来改变自己”,这是历史告诉许纪霖的和解之道。
眼下,许纪霖提及如今的理想型知识分子时,常常提到罗翔,“说出你的观点,往往比说服别人更重要”。他也有自己的自媒体“自留地”,“有自己的声音,哪怕和网红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我还能发声,还有一些人喜欢听我的声音,这就挺好”。
与时代和解,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在新时代依然有话要说,“内心有这份承担”。
《前浪后浪》是许纪霖又一次的进阶之作,他的研究方法,从思想史提高到精神史,即在1990年代的思想观念上做高一层,“不仅研究观念,还研究他的心态、精神、情感、意志的选择”。这样的尝试,“道理很简单”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活人感,不管在当下,还是历史中,都是稀缺品。许纪霖尝试将它打捞上来。
之所以做这样的研究,许纪霖并不讳言,是因为与自己的人生体验有关。“我永远是一个问题中人,这意思是,学问中人可以不在乎时代是什么,因为学问是一种脱离生命的智慧,它超越时代;但问题中人必须回应时代和人生的大问题。”
因此许纪霖认为,他的课题不仅是学术课题,也是人生课题,研究历史与观察现实,在他这里分不开、不存在断裂。“我的兴趣永远是想回答时代的困惑。”
许纪霖近年对青年话题感兴趣,这也是他的人生经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如何解释他们呢?虽然缺失了公共讨论的文本研究,但他直接进入青年文化的现场,同频他们的感受。这些也会成为他记录和分析的文本。
作为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许纪霖对许纪霖评价,或许会有独特的价值。“可能会说他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许纪霖解释,“我不会说这个学者提出了一套宏大的思想,或者做了一个经典式的研究,但是,如果要了解当下这个时代,恐怕以后的人会说,你可以读读许纪霖当时的研究。”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2985号